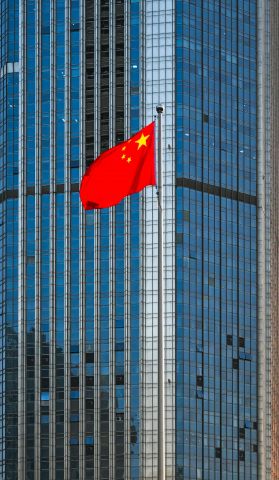
中國擁有現代世界歷史上最不均衡的經濟。很多産品的售價低於成本,其政策方針在於就業與生産目標,而非利潤目標,與西方國家、亞洲民主國家有著根本的不同。--史考特‧貝森特,日本經濟新聞專訪,2025.08.11.
解決產能過剩關鍵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政府無須干預。如果說過去在治理產能過剩方面有教訓,最大的教訓莫過於政府過多干預,過多救市。--趙振華,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怎樣認識中國的產能過剩〉,學習時報,2014.06.23
10月9日,中共商務部、環境運輸部公布多項針對美國的反制措施,當中對稀土進一步管制、長臂管轄,引發川普強烈不滿並表示將對中國祭出100%關稅,全球震動。隔天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解釋,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對合規者「將一如既往地予以許可」。北京此舉讓原本將在10月底APEC峰會期間進行的川習會出現變數,不排除是因應四中全會召開,展現對美國對中貿易制裁的強硬姿態,操作民族主義、淡化內部對經濟惡化的不滿;並主動出擊、拉高談判籌碼,逼川普對習近平提出的「不支持台獨」與「鬆綁高階晶片」做出讓步,因為,三輪談判後,習近平已看穿川普對「稀土牌」短期內很難有效應對。
儘管宣稱「一如既往」,但稀土管制是中共運用行政裁量卡全球脖子以遂其目標的工具,可快可慢、可鬆可緊,可賞可罰,增加產業鏈的不確定性與成本,升高貿易戰風險。近幾年中國經濟放緩而更加依賴出口,輸出大量低價過剩產能包括鋰電池、太陽能模組、電動車到歐洲、東南亞國家,引發激烈的貿易摩擦,包括美國與歐盟、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印度、南非、越南和泰國都祭出抵制措施,在中美貿易戰僵持之下,過剩產能爭議讓中國出口面臨更大壓力,也惡化其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否認產能過剩只談整治「內卷」
去年4月,美國前商務部長葉倫出訪中國,指出「中國的工業產能過剩可能會導致全球溢出效應」。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於去年5月對習近平表示「電動車和鋼鐵等受到大量補貼的中國產品正在大量湧入歐洲,世界無法吸收中國的過剩生產」,在今年7月中歐峰會上,馮德萊恩再次強調,產能過剩、與本國需求不匹配的補貼下的生產,都對歐盟市場構成壓力。
針對各國對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的批評,習近平一概駁斥,他強調,無論是從比較優勢還是全球市場需求角度來看,都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並表示歐洲面臨的挑戰並不來自中國。
10月7 日人民日報「鍾才文(中央財經委員會)」文章強力為「產能過剩」辯駁:「美西方一些人士將中國向國際市場提供高性價比產品誣稱為輸出過剩產能,將我與相關國家開展投資合作誣稱為補貼國有企業進行海外擴張。…中國企業競爭力來自充分的市場競爭,不存在大範圍、結構性的『產能過剩』,也沒有持續向外輸出『過剩產能』」。
中國政府並非一直拒用「產能過剩」一詞。2013年10月國務院就提出過「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政策文件,強調要推行供給側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唯近年中共將「產能過剩」說法視為「抹黑」與「意圖遏制中國發展」,在努力克服「西方卡脖子」、建立科技自主、應對貿易戰、實現偉大復興的敘事脈絡下,中共若接受此說,等同自認須承擔貿易失衡的責任。但此問題確已加重中國內外壓力,於是中共以「內卷式競爭」來替代,雖然避重就輕,但至少顯示習近平願意正視問題。
產能過剩:中共的「薛西佛斯巨石」
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開始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今年3月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
7月1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議強調要「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7月17日,人民日報刻意報導習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批判地方官員:「上項目,一說就是幾樣:人工智慧、算力、新能源汽車,是不是全國各省份都要往這些方向去發展產業?」顯示習確實認定上述產業已重複投資、產能過剩。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治理企業無序競爭」,「規範地方招商引資行為」。8月1日,發改委記者會表示,將制定「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行為防範事項清單」與修訂「價格法」,治理為壟斷而低價傾銷行為,將調查「內卷式」競爭突出的行業。
一系列宣示啟動新一輪「供給測改革」,其方法是禁止企業惡性低價傾銷與壟斷,要求地方政府加強招商引資信息的揭露、整治市場准入的壁壘。認定過剩與內卷是企業意圖獨佔,地方為政績、保護自身利益所造成的,將責任甩鍋給企業與地方,與中央無關。
產能過剩對中共來說不是新鮮事,建政後的各階段都發生重複投資、資源錯置的問題,歷經多次整治,過剩卻始終存在,猶如薛西佛斯的巨石,推上山頂後又滾回原點。
毛澤東時期:運動型計畫經濟與無效生產。生產計畫由中央主導,目標與實際需求不符,導致結構性的過剩加短缺。國企追求規模而非效率,重複建設、品質差、成本高。「大躍進」期間,鋼鐵產量要「超英趕美」,鋼產量從1957年的535萬噸飆升至1958年的1108萬噸,當中太多「土法煉鋼」的劣質品無法使用,形同無效生產,更排擠輕工業資源,導致民生物品長期短缺、大規模飢荒。
改革開放後:GDP至上、盲目擴張。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在1982年下達到2000年要「國民生產總額翻兩番」、年增長7%的目標,掀起大發展潮。1985年GDP成為考核地方官員績效的首要指標,為拉動GDP,全國競相投資工業與大型基礎建設,提供稅賦、融資、土地等優惠,豎起保護壁壘,限制外地產品與業者進入,各地追求自成體系、重複投資。到90年代後期,輕工業與消費品嚴重過剩,1995年工業普查,900多種產品中有一半產能利用率不到60%。2001年,年產3600萬台電視機,只能賣出1500萬台,冰箱年產2000萬台,但內需僅1200萬台。到2005年,約有90%產品長期供過於求。
2001年至2007年,中國加入WTO和房地產市場興起,內外需求增長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焦炭等基礎重工業擴張,但產能利用率低,鋼鐵產量佔全球1/4,利用率僅80%;水泥佔2/5,利用率僅75%。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加劇產能過剩,2011-2015年24個行業中19個過剩,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產能利用率都低於75%。
習近平新時代:製造業不能放,過剩永遠在路上
習近平的經濟思維很簡單,就是重製造、輕服務,要技術自主、趕超美國,強調「實體經濟是基礎,製造業絕對不能丟」[1],輕視服務業與網路產業,要「脫虛向實」、「科技立國」、「彎道超車」。習的思維注定其新時代終究要產能過剩,尤其是他一手主導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太陽能模組、鋰電池。
2022-2024年中國電動車年產量為705.8萬、958.7萬及1288.8萬輛,占全球市場64%、69%及74%,今年可達1675萬輛,大幅擴張導致競爭激烈、惡性降價、虧損倒閉。今年6月,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評論,2024年汽車業利潤率僅4.3%,今年第一季降到3.9%,「越造越賠」、「增收不增利」。2020年迄今中國已有超過8千家汽車經銷門市倒閉,中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指出,經銷商被迫降價出售大量庫存,賣越多虧越多,2019年整體淨利潤率為2%,2024年降至0,今年更跌至-2%,倒閉風險加劇。
2023年中國太陽能產業整體產量超過450GW,但同年全球需求僅為380GW;2024年超過1100GW,但2025年全球需求僅約600GW,平均產能利用率低於58%,去年超過50家企業破產清算或重整,5大龍頭企業合計虧損高達近340億元人民幣。鋰電池產業在電動車補貼政策拉動下盲目擴產,去年全球市占近八成,產能遠超需求三倍,領導大廠今年產能將達4800GWh,但市場需求估僅1000GWh,整體產能利用率低於4成。
產業不分高低新舊共同過剩
不僅在高新產業,鋼鐵、石化及煉油業等傳產到今天仍在過剩。2024年前8個月,中國鋼鐵業總虧損達169.7億人民幣,247家製造商中有95.7%處於虧損,4大上市鋼鐵業年度淨利總和不及1家日本製鐵,至11月整體債務攀升至5.1兆人民幣,創新紀錄。中國煉油產能全球最大,有6,000萬噸過剩產能,煉油與石化業今年上半年虧損較去年同期增加8.3%、超過12.5億美元。若不進行調整,到2034年前約10%煉油廠將被迫關閉。
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報告,中國產業政策的財政成本高得驚人,約占GDP的4.4%,每年約2%的生產力損失,形同GDP成長減少2%。數十年來,中共多次嘗試治療這個老症頭,但屢治屢發,甚至越打越旺。
朱鎔基時期推動國企改革,打出「三年脫困」目標,短期確有成效,50%國企完成公司化,國企虧損從39.1%降至20%;勞動生產率增85%;紡織、煤炭業負債率降至70%以下。但2003年開始,地方政府狂熱投入基建,鋼鐵、水泥再度過剩,大型國企更進一步壟斷市場,改革倒退。
習近平上台後,認為產能過剩將「影響到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大局」,為解決地方官員「GDP至上」風氣,他甚至曾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2]」。2015年他開始「供給測改革」,強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融入創新發展,之後鋼鐵、煤炭產能減少,盈利能力改善,企業債務占GDP比下降,創新投入增加,科技支出上升。
但舊的過剩處理完,卻在新的領域復燃。習推動「棚戶區改造」、漲價去庫存,推動中國房價上漲狂潮與泡沫破裂;他靠「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造成多國債務困境與工程爛尾。去年起宣示要「整治內卷」,8月對電動車業價格戰的禁令言猶在耳,業者轉頭就用免費保險、零利率貸款、免費充電等間接方式繼續削價競爭。而習更是緊抱GDP,陷在靠基建狂魔與製造業拉動GDP的路徑依賴中。
中共就是反覆產能過剩的根源
「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發展史的核心部分,總是以全國性的、運動式的、內卷式的樣態來呈現,其根源來自於中共的本質,即「黨管一切」下對「計畫」與「掌控生產要素」的堅持。中央主導產業方向與資源配置,讓不求利潤、效能低下的國企佔據優勢生產地位,以大量補貼、減稅、優惠等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導致市場失靈,生產與需求背離。加上GDP數字與政績、維穩的緊密掛勾,於是,中央訂目標、下指令、給資源(如半導體「大基金」),地方為達標升官而運動式競標,終局是重複投資與過剩。但地方基於就業、穩定、官位等考慮不願讓虧損企業退場,撐住大批僵屍企業,繼續消耗政府資源。這是中央與地方本於黨性交互作用的必然結果。
社會學者雷雅雯在其著作「鍍金的鳥籠」中有精闢分析:「撲天蓋地,運動式的規則制訂與執行。使企業非常難以計算風險與成本」,「其根本問題在於中國政府依賴績效而非選舉與法治作為主要的合法性來源和維持政治壟斷的動力」,「為維持其合法性與政治壟斷,中央領導層願隨著經濟危機週期、風險浪潮起伏及其自身需要,據以改變政策與信號[3]」,就是「一放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中共自身就是中國反覆產能過剩的根源。
幾乎所有專家都建議中共進行體制改革,移除行政干預,停止產業補貼,讓市場真正發揮功能,將資源重新分配、給人民應有的社會保障。但中共領導人都不去碰觸體制改革。這並非無能,而是理性選擇:黨的存續與個人權力比經濟更重要。內卷嚴重,就打擊重點企業;經濟惡化、感受不好,就用維穩手段來壓制不滿;但體制改革會衝擊黨內派系、菁英與利益集團,這對權力穩固是重大威脅。
習近平領航掌舵 駛向「完美風暴」
知名歷史學者馮克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書中指出,幾十年來,中國靠吸引外國資本、剝削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力、拍賣土地增加財政收入、政府補貼出口企業、組織國有企業集團到國外上市、借錢建設日後再還等手段達成經濟增長。如今,這些捷徑都已走到盡頭。中共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繼續壟斷政權和控制生產資料的前提下,解決由其自身所造成一系列長期形成的結構問題」,馮克的結論是:「看起來,前方只有死路一條」[4]。
四中全會前夕,日經新聞發布中國經濟學家調查,認為今年7-9月中國實際GDP預測平均值為同比增長4.6%,全年實際數字為4.6%,顯示中共無法達到5%目標。縱使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房貸利率調降與放寬限購、「以舊換新」補貼等,都無法提振因房地產崩跌、財富縮水造成的消費萎縮,產能過剩又拉低商品價格,進一步與通縮共構成向下的螺旋,加上高失業率、政府債務飆升,金融系統性風險升高,人口老化與負成長,疊加成一個「完美的風暴(Perfect Storm)」,作為掌舵領航的習近平,正朝向風暴駛去,中國經濟的長期躺平恐是難以迴避的命運。■
[1]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求是》,2020/21,2020-10-31,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
[2]〈習近平出席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中國政府網,2013.06.29,https://www.gov.cn/ldhd/2013-06/29/content_2437094.htm
[3]雷雅雯,《鍍金的鳥籠--中國的科技、發展與國家資本主義》,臺大出版中心,2025年2月,頁426-429
[4]馮克,《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聯經出版社,2024年2月,第334頁
作者 吳敏之 為政治工作者